
“美国新军工” 是近年来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和大国战略竞争加剧驱动下,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出现的全新发展模式和生态系统,以SpaceX、Palantir、Anduril等为代表的新型防务企业迅速发展,正在重塑传统由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五大军工巨头主导的军工产业格局。这一被称为“新军工”的现象不仅反映了科技革命、军事技术的代际更迭,也体现了美国国防战略、创新体系的发展模式转变。研究美国新军工发展新模式、新动态、新特点,对于加强我国防工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美国“联合发射联盟”的火箭搭载波音公司的航天器升空。图源:法新社
1
美国新军工的内涵与特点
“美国新军工” 是以大国战略竞争为目标、以发展颠覆性科技为核心、以建立快速敏捷机制为纽带、以运用科技创新资源为支撑,构建算法主导的作战理念、硅谷模式的研发机制与军民一体的创新生态系统,推动美国军事工业基础从机械化战争时代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迈进。
作战理念和战略导向牵引
美国新军工企业的快速发展不是单纯的市场现象,而是有着深层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理念支撑,反映了美军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技术路径。2024年1月,美国防部发布首份《国防工业战略报告》,明确提出通过代际变革构建更强大、更有弹性和更具活力的国防工业生态系统,其核心是推动国防工业基础从传统平台制造商向数字赋能者转型。报告坦承美国国防工业能力优势正在缩小,暴露出产能不足、人员短缺和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商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传统军工体系下难以解决,必须通过发展新军工模式实现突破。尤其是面对中国、俄罗斯等战略对手在新兴领域的追赶,美国将国防工业视为大国竞争的关键战场。国防部《国防工业战略实施计划》明确提出,提升弹药、导弹、潜艇等核心制造能力,强化供应链韧性(应对印太威慑需求),通过盟友合作(如 “奥库斯” 联盟)弥补产能缺口,加速无人作战等技术迭代;聚焦 “软件定义战争” 理念,构建以软件为核心、硬件为载体的灵活军事架构,通过发展新军工复合体提升美国在军工领域的优势地位。
前沿尖端技术创新成果爆发的驱动
美国新军工是市场前沿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结果,随着科学技术和新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AI)、大数据、量子计算、高超声速、太空技术、生物技术、网络技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尖端科技爆发,这些新兴领域的技术产品物化到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领域,正在彻底改变战争形态和军事能力需求。以往传统机械化、硬件中心化的军事体系逐渐让位于智能化、网络化、分布式的新范式,例如:AI 驱动的自主无人机集群(如安杜里尔的 “忠诚僚机” 计划)、战场决策支持系统(如帕兰蒂尔的 AI 作战平台);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精确制导武器(如 DIU 主导的 “复制者计划” 推动单价 15 万美元级巡航导弹研发),以及太空军事化加速(SpaceX 的星链军事化应用、太空军作战司令部的成立)。这些技术产品不仅改变了武器效能,更重塑了指挥控制、装备研制过程、后勤保障。新军工本质上是军事领域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核心在于将商业前沿技术快速转化为军事能力,新军工企业以数据为纽带、以算法为武器、以网络为战场,构建了全新的军事技术范式。Palantir公司开发的Gotham和AIP平台已成为乌克兰战场的数字大脑,乌军大多数打击目标都借助该平台实现从情报收集、态势分析到目标打击的全流程智能闭环,这标志着战争形态正从平台中心战向数据中心战转变。在技术架构上,新军工企业普遍采用数据获取—智能平台—作战应用的三层体系,极大压缩OODA(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时间。以SpaceX星链、遥感侦察、下一代GPS构成的数据获取层,形成了智能战场的神经末梢;以Anduril的晶格网格、Palantir Gotham平台为代表的基础平台层,构成了战场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作战应用层则通过AI生成作战方案、优化火力分配,实现决策与行动的一体化,这种架构使军事系统具备了类似互联网产品的快速迭代能力,将软件开发的敏捷性带入武器装备发展领域。
新兴领域高科技企业为主要创新主体
美国新军工代表企业,是以帕兰蒂尔(Palantir)、安杜里尔(Anduril Industries)、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为代表的硅谷系初创企业,它们凭借颠覆性技术(如 AI 数据分析、开放操作系统、可复用火箭)和敏捷创新模式,打破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 “五大军工” 长期垄断军方订单的局面。从企业基因看,这些公司大多由硅谷科技精英创立,将互联网思维植入国防创新过程。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重塑全球航天竞争格局。美国新军工企业呈现出与传统防务承包商截然不同的组织特征和商业模式,这些差异构成其颠覆传统军工体系的微观基础。帕尔默·勒基(Anduril)作为虚拟现实公Oculus的前创始人认为,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比美国军用车辆更好,iPhone的计算能力也比美国国防部常用系统更强大。未来的AI武器系统操作应像操作智能手机一样简单。在商业模式上,新军工企业普遍采用快速原型开发(Rapid Prototyping)方法,将产品开发周期压缩至传统军工企业的十分之一。安杜里尔公司形成了9-12个月出演示产品,1-3年完成全面部署的节奏,相比传统军工项目动辄十年以上的研发周期,这种硅谷节奏极大加快了军事技术迭代速度。SpaceX更是通过设计—开发—测试的快速循环,在星舰三次发射失败后仍能获得NASA持续支持,因其迭代试验方法大幅降低了研发成本和周期。
推进军民两用技术深度融合
OpenAI、谷歌等商业AI公司虽以市场商用为主体,但其基础研究成果通过技术溢出支撑服务军事AI;而军事应用的高标准又反过来推动商业技术可靠性的提升。SpaceX的星链系统在民用通信与军事侦察间无缝切换;alantirGotham平台既服务金融风控又指挥战场决策;Anduril的莱迪思操作系统同样适用于国土安全与边境巡逻,这种一种技术、双向用途的发展模式,既扩大了技术应用的规模效应,又模糊了军民技术界限,使商业技术进步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能力提升。各军种也建立了配套的创新促进机构。美国空军的“AFWERX”、特种作战司令部的“SOFWERX”等创新平台,通过举办创业挑战赛等形式,主动搜寻和培育有军事应用潜力的民用技术。在这些机构的推动下,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自主集群机器人等新兴技术快速进入军事测试阶段。硅谷民用科技(如社交媒体分析、商业航天)快速转化为军事能力,同时军方需求牵引民间研发。例如,DIU 通过其他交易授权(OTA) 绕过繁琐采购程序,允许初创企业 60 天内签订合同并快速迭代技术,打破传统军工 “烟囱式” 研发壁垒。这种军民双向转化促进机制,构成了美国新军工体系持续创新的深层动力。
建立全新科技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美国国防部通过设立如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国防创新单元(DIU)、战略资本办公室(OSC)等机构,推动新技术研发和应用。政府采用“其他交易授权”(OTA)等方式放宽规定,允许更大金额的投资协议,促进非传统军工企业成长。以硅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开始积极参与国防科技领域,带来了不同于传统军工企业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中情局的风险投资基金In-Q-Tel以及各类私募基金、创业孵化器等都在支持新兴防务公司的成长。中央情报局(CIA)的风投机构In-Q-Tel(IQT)、国防部国防创新单元(DIU)和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 通过资金注入、合同支持和孵化器合作,系统性培育 “使命驱动型” 军工科技企业。IQT 投资的 33 家初创企业进入 2024 年美国国家安全百强榜单,DIU 推动的 “企业测试载具” 项目旨在批量生产低成本巡航导弹。
制度设计和工作流程的变革
美国新军工的崛起不是个别企业的成功,而是整个国防创新体系变革的产物,其背后是美国政府精心构建的白宫—华尔街—硅谷工作模式。这一体系通过适应新科技企业发展的制度设计和资源配置机制,加速商业技术向军事领域转化。美国国防部已超越传统国防建设部的定位,兼具新科技部和新经济部职能,成为连接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的枢纽。在此框架下,DARPA负责颠覆性技术的预先研究,国防创新单元(DIU)聚焦民用技术军事化应用,战略资本办公室(OSC)则提供长期资本支持,形成覆盖技术全生命周期的创新管理链条。在具体实施层面,美国政府通过其他交易授权(OTA)等灵活采购机制,大幅降低了商业企业进入国防领域的门槛。DIU成立以来,OTA协议金额不断扩大,使安杜里尔等初创公司能够绕过传统国防采购的繁文缛节,快速获得军方合同。军地人才交流打破军工旋转门,前政府官员、军方高层转型为军工科技企业高管或投资人(如帕兰蒂尔招募前国防部、白宫顾问),使企业了解战略意图和军方需求,推动政策倾斜和订单获取;企业高管进入政府关键岗位(如国务院副国务卿提名),掌握企业创新发展特点规律,引入商业管理模式,提升了新军工企业的质量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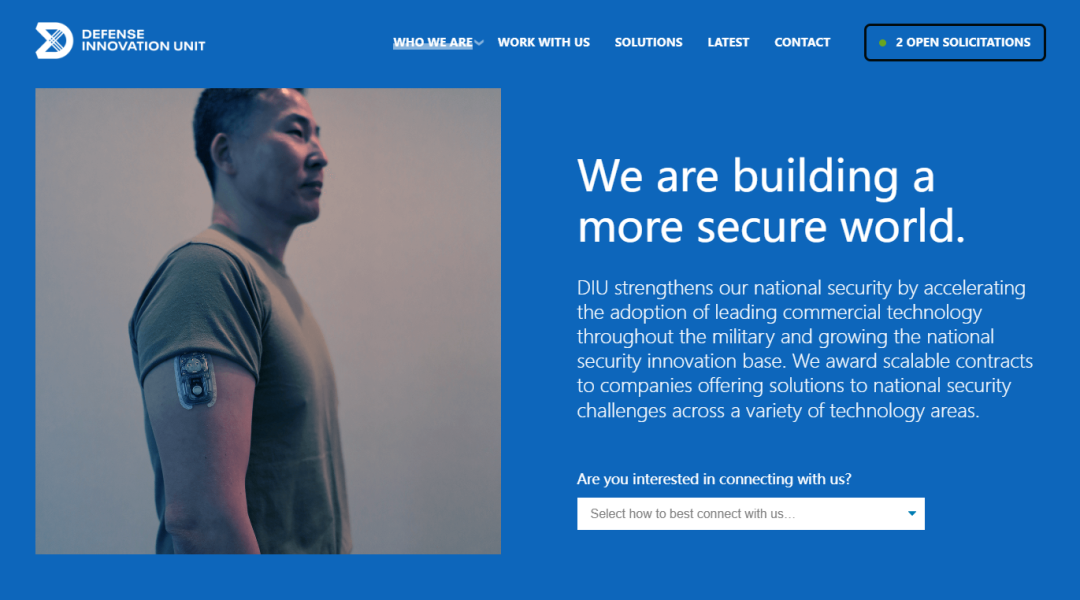
美国防创新单元 DIU网站。
2
新军工与传统军工的主要差异
美国新军工与传统军工相比,体现出一系列不同特点。
技术创新和发展速度的差异
新军工通常能够更快地将民用市场上的技术转化为军事用途,他们更加专注于快速迭代和创新,利用最新的商业技术和理念,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依托数字孪生、模拟测试和 “云边端” 架构加速验证,软件更新可实时响应需求迭代(如战场情报算法动态优化)。初创企业采用硅谷 “快速试错” 文化,SpaceX 通过迭代试验方法实现火箭技术突破,成本与速度远超传统航天系统工程模式。
传统军工公司由于规模庞大和官僚体制,技术研发周期较长,(F-35 战机从立项到部署耗时 20 余年),依赖物理原型测试,难以快速适应战场变化。俄乌冲突中暴露其弹药产能不足、电子战技术滞后等短板。装备采办实行成本加成合同制度,研发周期长达10年以上,如美军新一代导弹防御系统需数十年部署。
组织结构和灵活性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企业拥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决策过程更为迅速,可以快速适应市场和技术变化。采取任务型团队与弹性组织,政府机构(如 DIU)临时招募科技专家组建跨领域小组,打破层级限制;军工科技企业吸纳军方退役人员增强作战理解,形成 “需求—研发—部署” 快速闭环;资本多元化驱动创新,风险投资(IQT、硅谷资本)与政府订单结合,分摊前沿技术风险(如量子、高超声速领域),吸引私营资本长期投入。采用敏捷协作网络:OTA(其他交易授权)机制允许初创企业绕过繁琐采购程序,60 天内签订合同并快速迭代技术,打破传统 “烟囱式” 研发壁垒;企业高管兼具技术话语权与危机叙事能力,影响力从国会延伸至科技界与舆论场。
传统的军工科层制官僚结构导致决策迟缓,层级较多,决策链条长,采购程序僵化,难以吸引顶尖科技人才(薪资竞争力弱于硅谷)。这往往导致反应迟缓,在面对新的战略威胁时调整策略的速度较慢。依赖官僚化采购体系国防采办效率低,研发周期长,创新灵活性差。
目标定位和产品服务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支撑美军联合全域作战(JADC2)概念,整合陆、海、空、天、网、电多维战场,SpaceX 星链军事化部署提供分布式通信与侦察能力,AI 驱动的跨域指挥系统(如帕兰蒂尔平台)实现多兵种实时协同决策,安杜里尔巡飞弹增强印太地区分布式火力投送,构成 “数字—物理” 双重威慑体系。通过低成本规模化 + 全域渗透,以数量优势对冲高端装备代差(如 “复制者计划” 无人机集群),重塑大国战略竞争规则。新军工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往往更加注重软件定义系统、网络战能力、无人机和其他无人系统等现代战争所需的能力。军事能力 80% 依赖软件升级而非硬件更换(CSIS 报告),AI与自主化主导武器链,从侦察监视(AI 影像处理平台 “梅文计划”)、目标识别到自主决策(协同作战无人机 CCA),AI 深度渗透作战全链条。例如,安杜里尔的巡飞弹系统通过 AI 算法实现分布式协同打击,帕兰蒂尔平台为指挥官提供实时战场数据分析与战术建议,推动 “人在环上”(监督决策)而非 “人在环中”(直接执行)的人机协同模式。模块化与开放架构,采用开源操作系统(如安杜里尔 Lattice 系统)、商业标准接口(SpaceX 火箭复用技术)和 API 驱动集成,降低技术整合门槛。分布式作战、马赛克战等新形态均基于此架构展开,支持低成本武器快速规模化部署(如 DIU “复制者计划” 推动数千架低成本无人机集群)。
传统军工主要聚焦单域优势(如空中优势、海上控制)和大规模平台(航母、隐形战机),服务于冷战及反恐战争线性消耗战逻辑。侧重于大型硬件平台,比如战斗机、舰艇和坦克等重型装备。通常以硬件为中心,依赖物理装备迭代,作战效能提升依赖机械性能升级。创新路径受制于封闭供应链和独家技术保护,对新兴技术(如 AI、量子计算)整合缓慢。
军工组成主体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以硅谷系科技初创企业为主体,如帕兰蒂尔(Palantir)、安杜里尔(Anduril Industries)、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等凭借颠覆性技术快速切入市场。例如:SpaceX 的可回收火箭技术使太空发射成本降至传统方案的1/10 以下,迫使波音与洛马合资的 ULA 联盟边缘化;帕兰蒂尔的 AI 平台在乌克兰战场充当 “数字大脑”,市值一度超越雷神、波音等传统巨头。初创企业依赖政府深度孵化生态:中央情报局风投机构In-Q-Tel(IQT)、国防部国防创新单元(DIU)和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通过资金注入、合同支持和孵化器合作系统性培育新力量。IQT 投资的33 家企业进入 2024 年美国国家安全初创企业百强榜单,DIU 推动的 “企业测试载具” 项目旨在批量生产单价15 万美元级巡航导弹(传统导弹单价 100 万–400 万美元)。
传统军工主要由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技术(RTX)、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等 “五大军工巨头” 长期垄断军方订单。这些企业通过规模效应、纵向整合供应链(如自研发动机、电子系统)和政治游说网络控制市场,政府订单占其营收的70% 以上。项目复杂性导致预算超支和交付延迟成为常态(如 F-35 战机成本失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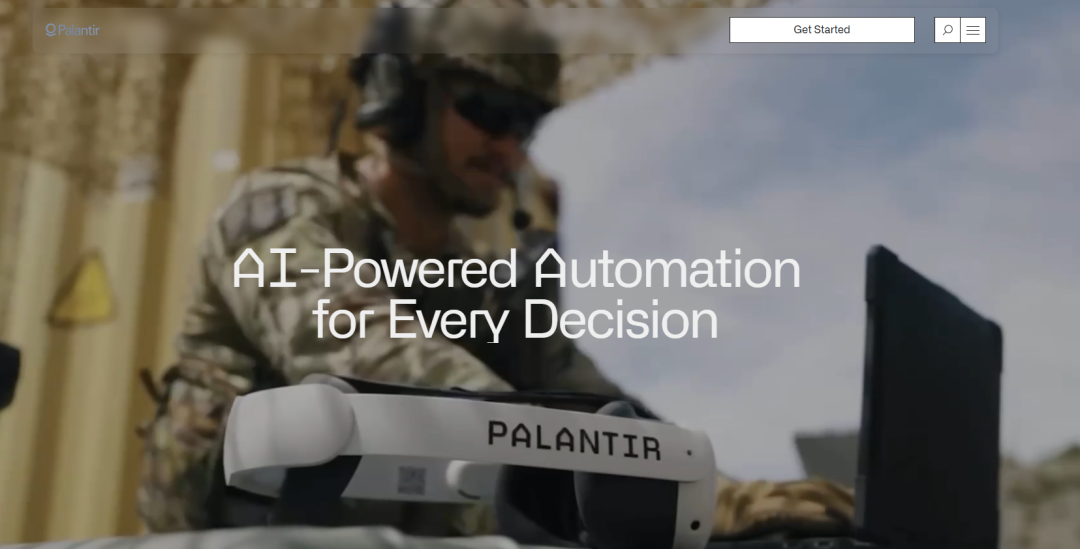
帕兰蒂尔(Palantir)网站。
创新主体合作生态方面差异
新军工企业积极参与到一个由初创公司、风投机构、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广泛生态系统中,构建弹性与备份供应链体系,模块化设计与激增能力,武器系统采用标准化接口(如 DIU 推动的低成本导弹项目),便于战时快速扩产。国防部通过GOCO(政府拥有承包商运营)模式、税收激励和战略资源储备,要求军工体系具备战时产能放大数倍的弹性(应对印太威慑或大规模冲突需求);全球协作弥补缺口,通过盟友合作(如 “奥库斯” 联盟共享核潜艇 AI 技术)分摊研发成本、加速技术迭代,削弱本土产能瓶颈制约。
传统军工则更多依赖于既定的供应链和长期合作关系,这些关系相对固定,不太容易改变,依赖纵向整合封闭供应链,关键环节(如先进芯片、特种材料)存在单点风险。俄乌冲突过程中暴露弹药储备不足、产能爬坡缓慢问题,凸显对规模化激增生产准备不足。
国防预算和采购效率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通过技术实力 + 危机叙事构建复合影响力,企业高管(如帕兰蒂尔 CEO)频繁发声渲染美国面临的威胁,将技术发展与国家安全叙事绑定,话语权跨越科技界、政界与媒体,游说国会增加 AI、太空等领域投入(2025 财年国防预算增幅创十年新高);以 AI 分析平台、自主系统、太空基础设施构建 “数字边疆”,通过盟友技术扩散(如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 AI 技术)强化联盟控制力,削弱竞争对手区域影响力。初创企业市值快速扩张(帕兰蒂尔 2024 年市值一度达 1732 亿美元,2025年将达3000亿美元,超越任何一家传统军工企业),反映资本市场对其颠覆潜力认可,进一步撬动政策倾斜。
传统军工依赖政商旋转门游说和 “就业保护” 叙事争取预算(如特定选区军工就业关联),但近年面临波音军工部门亏损、股价下跌等竞争力下滑压力。影响力基于政商旋转门网络和政治献金,主要作用于国会防务委员会及军方采购体系。
研发成本方面的差异
新军工研发成本更具优势,SpaceX 可回收火箭使太空发射成本降至百万美元级;安杜里尔巡飞弹单价仅为传统导弹的1/10 至 1/20;DIU 推动的低成本巡航导弹项目将单价压至 15 万美元级,实现 “数量换质量” 优势。软件主导降低长期成本,装备效能升级依赖软件更新而非硬件更换,减少全周期投入。军民技术池分摊研发风险(如商业卫星星座部分承担军用侦察任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传统军工因复杂性导致成本失控(F-35 项目超支数千亿美元)、采购单价虚高(导弹单价百万美元级),全生命周期维护费用高昂。常常面临产能过剩(如 F-22 停产)、技术迭代滞后(电子战、高超领域追赶中俄)及供应链脆弱性(关键芯片依赖海外)问题,且体系惯性强、转型阻力大。部分核心技术(如先进半导体、稀土材料)仍依赖海外,与 “制造业回流” 目标冲突,地缘政治扰动易冲击生产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3
美国发展新军工动向对我国国防
工业的启示
美国发展新军工(New Defense Industrial Base)的根本目的是应对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战争,归根到底是应对大国竞争和技术革命浪潮,其核心在于颠覆传统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MIC)的封闭垄断、官僚僵化和硬件主导模式,转而构建以硅谷创新生态、软件定义战争、敏捷机制和军民一体化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型国防工业体系。新军工不仅重塑了美国军事力量生成机制,更对全球军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我国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完善国防采办制度,带来深刻启示。
启示之一,应当高度重视新兴领域科创企业的技术产品,将其快速转化为军事应用
美国的新军工企业注重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大数据平台等,将其转化为军事应用。我国也出现了如华为、京东、DeepSeek、腾讯等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将我国民用领域科技创新性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应用到武器装备研制生产领域,从而对装备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全面提升我国武器装备研制生产能力和战略竞争力。应当加大对战略前沿领域掌握核心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集中攻关装备发展“卡脖子” 领域,在半导体与材料攻坚方面,加速光刻机、先进芯片制造、稀土永磁体等产业链自主化,降低对美日欧技术设备的依赖;在工业软件与设计工具方面,发展自主 EDA、仿真平台和数字孪生系统,避免军工设计受制于海外软件断供;在颠覆性技术源头创新方面,在量子、AI、高超音速等领域建立原始创新能力。
启示之二,应当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构建敏捷响应、快速转化机制
新军工企业拥有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决策过程更为迅速,可以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变化,通常采用敏捷协作网络:OTA(其他交易授权)机制允许初创企业绕过繁琐采购程序,60 天内签订合同并快速迭代技术,向军事领域转化渠道快速有效。我国新兴领域科技创新企业具有强烈的报国愿望,但因受制于需求信息、参军资质、入门权限、审批流程、保密等因素,往往很难进入国防领域。应当根据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特点,跳出传统的预研、定型、采购、制造的程序办法,另辟蹊径,根据新兴领域产业发展特点,研究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进入国防领域的特殊办法,建立新质生产力快速进入军事领域的通道,赋予主管部门职能,设置发现、评估、培育、投入、采购、应用形成全链条闭环的机制。
启示之三,应当下决心破除两大体系之间的壁垒,构建军民一体化先进制造业体系
美国通过建立军民两用技术及产业发展体系,鼓励民用高新技术应用于军事领域,同时也让军事技术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我国可以借鉴参考这种模式,促进军民一体化先进制造业深度发展,实现资源共享和技术转化。破除传统的自成体系模式,融入大生态,推进 “小核心、大协作” 体系,平衡 “尖端威慑” 与 “低成本规模消耗战” 能力,如发展模块化、易升级的导弹系统(参考 DIU 低成本导弹思路)而非单一追求极致性能。推动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融合(如商业航天发射接口兼容军用载荷),实现资源高效配置;依托市场化平台驱动,依托国家高技术转化基地、产业联盟等载体,建立技术交易市场、创新孵化器及融资对接机制,促进军用需求与民用技术精准匹配(如 AI 算法军民转化枢纽)。
启示之四,应当把优化工作流程和提升效率放到突出位置,创新工作运行模式
新军工企业通常拥有更加灵活的商业模式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我国可以考虑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式,优化军工企业股权结构,激发企业活力,提高运营效率。扩大竞争性采购范围,探索 “快速原型验证—小批量试用—规模量产” 的敏捷路径,借鉴 DIU“需求导向、市场筛选” 模式引入民企技术(如商业航天测控转化军用通信);建立类似 DIU 的军事需求快速对接平台,临时招募科技专家组建跨部门小组(打破科层限制),推动 “需求提出→研发验证→战场部署” 闭环加速;将军方实战经验(如退役指挥官)融入科技企业研发团队,同时吸引顶尖民用科技人才参与国防项目(提高薪资竞争力、职业发展空间),破解传统军工 “技术吸引力不足” 困局。
启示之五,应当高度重视军工主体的内生动力,构建开放合作的创新生态系统
美国新军工的成功离不开一个由科技初创公司、风险投资机构、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组成的良好创新生态系统。我国可以根据国情、军情、军工生产等特点,构建军方、军工、政府、科研机构、民企广泛合作的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吸引更多民口高新技术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国防建设,推动人工智能、网络、新能源、商业卫星遥感、消费电子、5G/6G 通信、云计算、大数据、智慧物流等民用技术快速适配国防场景,建立军民通用技术标准与接口(如开源操作系统、API 驱动模块化集成)。健全军方需求牵引和技术创新推动对接机制,推动外层空间、网络空间、临近空间、深海探测、认知领域等的需求牵引民口企业研发,通过需求发布(如 “揭榜挂帅”)、预研合作(参考 DARPA 探路机制)引导私营资本投入无人和反无系统、定向能、量子通信等战略前沿领域,同时将军用先进成果反向注入民用产业。加大军民协同攻关力度,鼓励跨领域协作创新,避免传统军工的 “烟囱式研发孤岛”, 采用开放架构(如类似 Anduril Lattice 的开源作战系统)降低整合成本。破除封闭壁垒,规范保密定密权限、知识产权归属等政策,降低民口企业参与门槛,形成双向技术溢出闭环。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持体系,出台支持民企参军的数据资源共享、税收优惠、人才引进、金融扶持等优惠政策,促进军民一体化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
(作者:顾建一,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工业和信息化部重大战略服务专家,军事科学院战略评估咨询中心特聘专家。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值班编辑:白 雪、显 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颜楚凌
值班总编:闫金久